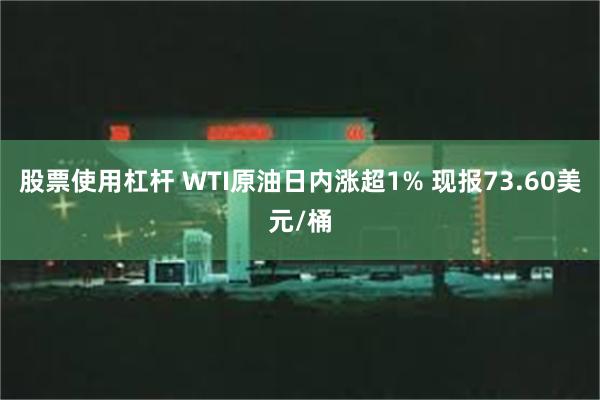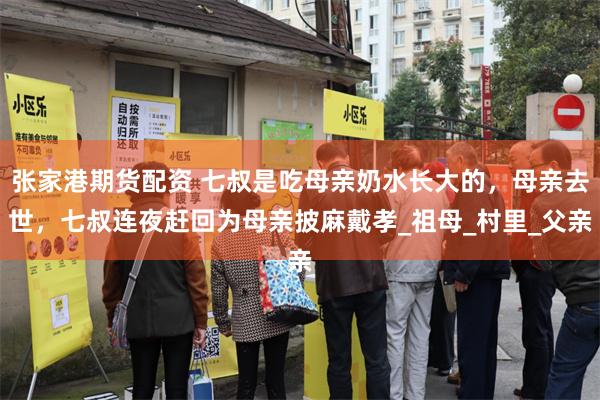
"记住张家港期货配资,我走后,一定要穿咱娘做的那件麻布孝衣。"这是七叔顾明安临终前抓着我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他的手指瘦骨嶙峋,却有着惊人的力道,仿佛要将这份嘱托深深刻进我的骨髓里。
那是1978年的寒冬,北风呼啸,天色阴沉得让人心里发慌。我接到电报从县城赶回村里时,七叔已经躺在那张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旧木板床上,面色灰白,呼吸微弱。
屋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,昏黄的灯光在墙上投下摇曳的影子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药草的苦涩气息。
七叔不是我的亲叔叔,他姓顾,我姓张。在我们村里,称呼向来是按照辈分顺序排的,我爹排行老六,七叔就是第七位,虽然没有血缘关系,却是我们家实打实的一份子。
关于七叔的身世,村里有许多传言。我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,七叔是在抗战时期,被炮火轰炸后从废墟中救出的孤儿。
"那年啊,鬼子的飞机像蝗虫一样飞过来,炸得天都黑了。"村里的老支书每次提起这事总是这么说。
七叔那时才三岁,全家遇难,只有他躲在灶台下活了下来。当民兵从废墟里把他刨出来时,小小的身体已经冻得发紫,眼睛里满是惊恐与无助。
展开剩余92%我祖母张秀兰当时刚生完我父亲,奶水充足。她经过那片废墟时,听见有人说找到了个孤儿,二话没说就把他抱回了家。
"娃啊,别怕,从今往后,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"祖母抱着那个瑟瑟发抖的小身体,轻声说道。
从此,七叔和我父亲一起吃我祖母的奶水长大,成了"奶兄弟"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多一张嘴意味着全家都要更紧一紧裤腰带,但祖母从未有过半句抱怨。
"那时候你祖母多好啊,"村里的王大娘常这样对我说,一边用布满老茧的手搓着玉米棒子,一边摇头感叹,"别人家连自家孩子都养不活,她还收养了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儿。秀兰那心啊,比这井水还深,比这天还宽。"
我从小就听着七叔的故事长大。祖母常说:"命是苦的,但人心是甜的。"这话用在七叔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
七叔比我父亲大半岁,从小就懂事。他五岁就能帮着放羊,七岁会砍柴挑水,十岁能帮着下地干活。记得祖父常说:"明安这孩子,心里有一本账,恩情记得清。"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。当时在县里中学读书的七叔主动提出到农村支援建设。他被分配到了我们村的生产队,成了一名正式社员。
那时候,我父亲已经在公社当了会计,每个月能拿到二十八块钱的工资,日子过得比村里人强多了。
"六子啊,你留在公社挺好,明安就留在村里照顾爹娘吧。"祖父拍着七叔的肩膀说,眼里闪着欣慰的光。
那时候,七叔有机会返回城里工作。公社书记看中了他的才干,想让他去管仓库。但七叔拒绝了这个难得的机会。
"为啥不去啊?"我父亲不理解,"在公社比在队里强多了,又不累,还有固定工资。"
七叔只是摇摇头,淡淡地说:"老人家一个人在村里,我不放心。再说了,我这辈子欠娘的,啥时候还得完?"
祖父去世后,七叔更是寸步不离地照顾祖母。每天早上,村里人都能看到七叔推着自行车带着祖母去集市。
那是一辆老式的永久牌自行车,黑漆都磨得发亮。祖母年纪大了,腿脚不便,七叔就用木匠的工具,在自行车后座绑了个小木板,上面还铺了块棉垫,让祖母能坐得舒服些。
冬天里,他怕祖母冻着,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垫在木板上,只穿一件单薄的蓝布褂子骑车。多少次,我看见他的手冻得通红,却仍笑呵呵地对祖母说:"娘,不冷,一点都不冷。"
七叔和祖母的感情,是村里人常挂在嘴边的话题。每到农闲时节,村里人喜欢搬着小板凳坐在大槐树下乘凉,七叔和祖母的故事总能引起一阵感叹。
"想当年,多少人劝秀兰别多事,别收养外姓的孩子。现在看看,这个外姓儿子,比有些亲生的还孝顺呢!"王大娘总是这么说,说完还不忘瞪一眼自己的儿子。
村里人都说,七叔和祖母之间有什么秘密。每到月初,七叔总会独自进城一趟,回来时手里提着一个蓝布包袱。
"是不是明安在城里有对象了?"有人这样猜测。
"哪有对象啊,都四十多了,还一个人。"
"那包袱里装的是啥?"
"兴许是药品吧,老太太年纪大了。"
也有人说是城里的稀罕物什。三叔的婆娘就曾偷偷翻过七叔的包袱,却只发现了一些普通的糖果和点心。
"装神弄鬼,"三叔的婆娘撇着嘴说,"不就是些糖果点心嘛,搞得跟宝贝似的。"
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,那是七叔攒下的工分,换成钱给祖母买的营养品。三年困难时期,正是这些东西救了祖母的命。
那时候,生产队里按工分分口粮,七叔干的是最重的活,每天能挣十分。他总是把自己的粮食省下来,换成钱,再去县城的国营商店买点祖母爱吃的点心。
"我年轻力壮,饿两顿没事。娘那么大岁数了,得补一补。"七叔总是这样解释。
七叔一辈子没结婚,村里不少人背后议论纷纷。
"听说当年有个女知青看上他了,给他写信,他都没回。"
"那是,看他那样,也养不起媳妇。"
"我看啊,他就是个傻子,为了个没血缘关系的养母,搭上自己一辈子。"
每次听到这些闲言碎语,七叔总是笑笑不说话。只有我知道,他的抽屉里藏着一封泛黄的信,信上有个女孩子清秀的字迹:"明安同志,我愿意和你一起留在农村,照顾老人..."
信的末尾,是一行被水迹模糊的字:"如果你能放下那个老太太,我们就......"
七叔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封信,也从未去找过那个女知青。他只是每天如常地照顾祖母,干着生产队里最累的活,脸上总是挂着平静的笑容。
去年冬天,祖母病重。那天刚下了一场大雪,村里的小路上积雪厚厚的,连出门都困难。我连忙托人捎信给生产队,七叔正在田里干活。
听到消息,他放下锄头,连饭都没吃,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。那天晚上下着大雪,路上积雪厚厚的,但七叔硬是用了平时一半的时间赶回了家。
当他推开门的那一刻,我看见他的裤腿全湿了,脸上挂着汗珠和雪水的混合物,眼睛里却是无比的清明和坚定。
我至今记得七叔跪在祖母床前的样子。他用一块青布包着头,腰间系着一条粗麻布带,这是我们这里传统的孝服装束。他披麻戴孝,额头抵在祖母的手背上,肩膀微微颤抖。
"娘,儿子来晚了。"他低声说,声音沙哑,却异常清晰。
祖母已经说不出话来,只是用干枯的手轻轻抚摸着七叔的头发,眼角有泪水滑落。她的眼神里满是不舍和牵挂,却又带着某种释然。
"娘,您放心走,儿子没啥本事,但这辈子没给您丢过脸。"七叔的声音颤抖着,却坚定无比。
祖母的嘴唇动了动,似乎想说什么,最终只是轻轻点了点头。那一刻,屋子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墙上老挂钟的滴答声,和祖母微弱的呼吸声。
祖母临终前,将一个小木盒交给了我父亲,嘱咐说:"这是咱家的传家宝,给明安。"
父亲打开木盒,里面是一块翠绿色的玉佩,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。玉佩不大,却通透温润,上面刻着一个"福"字。
"他虽不是我亲生的,但吃我的奶水长大,和你一样是我的儿子。这块玉,是我爹临终前给我的,说是保家宅平安的。"祖母用微弱的声音说,"明安这辈子没成家,以后就靠这个保平安吧。"
这事引起了一些亲戚的不满,尤其是我的三叔。他在收殓祖母的那天,看着七叔手里的玉佩,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晚上,在为祖母守灵的饭桌上,三叔终于忍不住了:"外姓人拿走咱家的传家宝,说得过去吗?你们谁家是这么做的?"
桌上一时安静下来,只听见酒杯和筷子碰撞的声音。我父亲想说什么,但被七叔拦住了。
七叔听后没说话,只是默默站起身,将那块玉佩放在桌子中央,然后离开了饭桌。那一晚,他守在祖母的灵床前,一夜未眠。
一周后,土葬完祖母,他把所有亲戚都叫到了家里。只见桌上摆着十几个小木盒,每个盒子里都有一块小玉坠。
"这是我请城里师傅把玉佩切成的小件,每家一个,大家都是一家人。"七叔说着,将木盒一一递给在场的亲戚。
我打开盒子,发现玉坠背面刻着"秀兰之子"四个小字。那一刻,我看到了三叔眼中闪过的愧疚。他低着头,接过木盒,竟一时语塞。
"三哥,咱娘生前最怕的就是咱们兄弟不和。她把玉给我,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强,而是怕你们嫌弃我是外姓人。"七叔平静地说,眼里没有一丝责备,"但在我心里,你们永远是我的亲兄弟。"
那天晚上,三叔破天荒地留下来和七叔喝酒,两人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。酒至半酣,三叔突然红了眼眶:"七弟,这些年是哥对不住你。当年分家时,我拿了最好的那间房,还多分了两亩水田..."
七叔摆摆手:"都过去了,咱娘活着的时候,我就没计较过。现在她走了,咱们更该好好的。"
那晚过后,三叔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。他开始隔三差五地来看七叔,有时候带点自家做的豆腐,有时候提壶烧酒,两人能坐在院子里聊到深夜。
七叔一生未娶,孤独地生活到了六十三岁。他最后那段日子,是在我家度过的。他的病来得很突然,医生说是肺心病,怕是积劳成疾。
"还不是当年下冬水整地落下的病根。"王大娘叹息道,"那时候大雪封村,他非要下水田修渠,说是春天好浇麦子。结果大病一场,从此落下了病根。"
临终前,七叔握着我的手,说了那句要穿祖母做的麻布孝衣的话。我这才知道,祖母生前亲手为他缝制了一套麻布孝衣,说是等她百年后,让七叔披麻戴孝,以全孝道。但七叔舍不得用,一直珍藏在柜子底层。
"我这辈子,欠娘太多了,临了能穿上她给我做的这身衣服,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。"七叔微笑着说,眼里满是释然。
他走后,我按照他的遗愿,为他穿上了那件祖母亲手缝制的麻布孝衣。那衣服虽旧,但洗得干干净净,叠得整整齐齐,仿佛承载着某种神圣的仪式感。
奇怪的是,当我打开柜子找那件孝衣时,发现它旁边还放着一沓泛黄的信纸。那是祖母写给七叔的信,字迹歪歪扭扭,显然是个不识几个字的老人家请人代笔的。
信中写道:"明安啊,娘知道你为啥不娶媳妇,是怕别人说闲话,说你是外姓人,配不上好人家的姑娘。娘想告诉你,你比谁都好,值得最好的姑娘。别为了娘耽误了自己..."
每封信的末尾,都是祖母亲手按的红手印。看着那些已经模糊的指纹,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更让我意外的是,在信纸下面,还有一个小布包,里面是七叔这些年来的存折。存折上的数目不多,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存入记录。折子夹层里有一张纸条:"此为明安积蓄,百年后用于养老院捐赠,为老人办实事。"
下葬那天,全村的人都来了。老支书特意穿上了他唯一的一套中山装,佝偻着背,站在坟前久久不愿离去。
"好人哪,真是个好人..."他不停地喃喃自语,眼眶湿润。
王大娘带着她的孙子孙女来了,他们手里捧着几朵野菊花,恭恭敬敬地放在七叔的坟前。
"记住这个叔叔,"王大娘对孙子说,"他教会我们,人活一辈子,不是图啥名声,而是心里装着谁。"
最让我意外的是,竟然有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从县城坐车赶来。她在人群后面站了好久,等大家都散去了,才慢慢走到坟前,从怀里掏出一封泛黄的信,默默地放在坟上。
"这是谁啊?"我好奇地问三叔。
三叔眯着眼看了半天,才恍然大悟:"哦,这不是当年那个喜欢七弟的女知青吗?后来她嫁到县城去了,好些年没见了。"
我站在坟前,想起七叔生前常说的一句话:"人这一辈子,不在乎活得长短,而在乎心里装着谁。"
是啊,七叔的一生,心里装的都是那个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养母。他用自己的方式,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孝道。
走的时候,我摸了摸胸前挂着的那块玉坠。这是七叔留给我的,背面除了"秀兰之子"四个字外,还多了一行小字:"恩情无涯,心中自明。"
血缘虽重,恩情更深。真正的亲情,从来不是血脉相连那么简单,而是在患难与共中,心与心的相依相守。
回县城的路上,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。我想起小时候,七叔曾背着我去看麦子出芽,他指着绿油油的麦田说:"看见没,种子埋在土里,不见天日,但它知道往哪个方向生长。人也是一样,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,就知道该往哪里去了。"
我忽然明白,七叔此生最大的幸福,不是得到了什么,而是他始终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这份知道,让他的生命尽管坎坷,却始终笔直如青松,挺拔如日出。
对于七叔来说,那件麻布孝衣不仅是一件衣服,更是一份承诺,一种归属,一个终生不渝的决定。穿上它,他完成了自己作为儿子的最后仪式,也完成了对养育之恩最庄严的回报。
雨越下越大张家港期货配资,却没有丝毫的悲凉。我仿佛看见七叔穿着那件麻布孝衣,微笑着向祖母走去,步履轻盈,再无牵挂。
发布于:内蒙古自治区